多年之后我們回眸今天,一定會慶幸當初選擇了氫能,才得以化解讓地球洪水滔天的氣候危機。
BP最新年度能源統計報告顯示,2021年,全世界直接使用化石燃料而排放的二氧化碳達到340億噸,如果算上泄露的甲烷和其它溫室效應氣體,總排放相當于390億噸二氧化碳。按照現在的節奏,別說實現控溫1.5°C的目標,2°C的目標都可能落空,借用BP首席經濟學家Spencer Dale先生的話說就是,世界依然走在不可持續的道路上。
如何改弦易轍才能夠走向可持續發展呢?盡快減排,盡最大量減排是唯一的選擇。毫無疑問,綠色電力,也就是可再生的光伏太陽能和風能將是減排的主力軍,但在光伏和風能裝機飛速增長的情況下,如何能保證不再有棄光棄風的事情?如何解決由于光伏和風能資源分布與負荷中心錯位的問題,是長距離高壓輸電還是用天然氣管網來輸氫,哪個更合算?
另外,在終端能源消費電氣化率受限的情況下(假設最高達到80%),如何在剩余的能源消費領域實現減排?還有,儲能在能源轉型中有著難以替代的作用,但是如果在規模上要提高幾個量級,鋰電池怕是難當大任,這還沒有考量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影響的評估。此外,那些重要但是目前難以減排的領域比如鋼鐵航運等等怎么辦?解決這些問題,氫能幾乎成了獨一無二的選擇。
氫能真的靠譜嗎?
綠氫生產成本穩步下降
氫能可以簡單分為灰氫(化石能源制氫)、藍氫(化石能源制氫+碳捕捉與封存技術)、綠氫(可再生能源零碳排制氫)三種,可持續發展需要的是綠氫,綠氫的成本主要取決于綠電和電解槽。
意大利天然氣管網公司(SNAM)原CEO馬可·阿爾維拉先生在《氫能革命》一書中,對于綠電成本,電解槽成本和綠氫的成本有一個很好的總結,我借用如下:
可以看出,在過去10年間,綠電成本下降到了原來的十分之一。而在未來10年中,電解槽裝置規模將增加十幾倍到上百倍,而電解槽的資本支出(也就是一次性購買成本)將下降到今天的1/4,這樣綠氫的生產成本將下降到2021年的1/3左右,達到$2/KG, 按標準熱值天然氣測算,美元人民幣匯率按1:6.8計算,2025年綠氫成本相當于每立方天然氣人民幣3.7元,2030年相當于每立方天然氣2.80元人民幣。與當下天然氣的市場銷售價格相當。
我認為,對于電解槽裝置的資本支出測算有些保守,在中國制造的實力基礎上,如果既有訂單再有補貼,電解槽裝置成本下降會比較快。
另外,很多人擔心,綠氫生產耗水太多,這其實不用太擔心。每噸綠氫生產需要耗費淡水大概9噸左右。這樣,中國十四五氫能規劃中2025年產10萬噸綠氫(相當于3.6億方天然氣)生產將耗水90萬噸,折合每方天然氣耗水2.5公斤。歐盟在RePower EU計劃里提出到2030年實現1500萬噸的氫能年產量, 總共年耗水1.35億噸水,這可是相當于550億方天然氣的巨量能源。另外,綠氫使用完畢生成物也是水,也基本實現了循環經濟。
氫能可借力天然氣管網
說完制造我們再來看看運輸。如果是摻混到天然氣管道,那么簡單說運輸成本和今天槽罐車相比就變得非常有競爭力。能否摻混到天然氣管道?一般來說,因為氫分子很小,它可能穿透管道的鋼質材料,從而引起所謂氫脆的問題。這其實是和管道的材質有很多關系,如果是軟鋼,而且管壁較厚,那么發生氫脆的可能性很低而且會很慢。
SNAM公司在意大利已經完成的試驗表明,意大利95% 以上的天然氣管道都可以摻混氫氣,70%以上的天然氣管道甚至可以運輸100%的純氫。如果管道因為材質的原因不能摻混,那就要看具體情況進行升級。這無疑會產生較大的成本,但是管道本身也是有壽命的,也需要不斷更新。事實上,如果是新建管道,現在的材質更多都是PVC塑料材質,不僅耐用結實,輸氫完全沒有問題。

在管道更新方面,英國領跑全球,正在更新其大部分天然氣管道。歐盟也有由23家能源運輸公司發起的氫能骨架計劃,預計到2040年,歐洲將有4萬公里的輸氫管道。
氫能的主要神奇之處還在于它能夠通過天然氣管網設施(運輸存儲甲烷分子),通過氫能燃料電池與電網(電子流動)耦合互補,實現跨區域,跨季節的調節作用。這時候,就會面臨到底是通過高壓電網長距離輸電,還是通過天然氣管網輸送氫能?我認為看電網或者管網哪個更有效即可。如果是已有電網且容量有余,就可以考慮輸電;如果沒有富余電網,但是有天然氣管網,那就考慮管網輸氫。如果都沒有,必須新建基礎設施,需要從距離、已有配套設施、負荷中心具體需求等方面做完備詳細的分析,沒有唯一的答案。
無論如何,綠電和氫能,通過電網和天然氣管網,將成為真正的能源雙雄。
運輸問題解決后,就是儲氫的問題了。其實天然氣管道本身就是體積巨大的儲氫場所,因為加壓就可以增加管道里的存量。而更讓人欣喜的是,可以將氫儲藏于地下鹽穴儲氣庫。鹽穴壁致密結實,能夠承受20兆帕以上的壓力,體積在幾萬到上百萬立方米,是儲氫的理想場所。雪佛龍公司在美國德克薩斯利用鹽穴儲氫有幾十年的歷史,英國有三處鹽穴儲氣庫都用來儲氫。
鹽穴之外,廢棄天然氣田雖然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儲存天然氣,但是否也能用來儲存氫氣,需要認真研究做可行性分析。比較棘手的問題是,氫分子十分活躍,有可能和其中的微生物,硫或者巖石中的礦物質發生化學反應。但是總體來說, 地下儲氣庫的儲藏成本在$10/MWH, 和制造運輸成本相比還是很小的。
解決了制造運輸儲藏的問題,許多人仍然擔心氫是否能夠替代其他能源, 我對此非常樂觀。在許多工業領域尤其是難減排行業,還真是非氫能莫屬。
氫進萬家早已有之
在天然氣發電領域,大型燃氣輪機發電,據西門子最近的報告,可以摻混75%的氫。國內也已經有類似的試驗,2022年6月,國家電投下屬的北京重燃已經啟動了燃氣輪機摻氫30%的試驗。燃氣小鍋爐改為燒氫氣或者氫氣天然氣的混合氣體也都是能做到的。
在家居端,其實我們使用氫也早有歷史。在天然氣還沒有大規模進入城市之前,我們家里用的都是人工煤氣,其主要成分是氫氣和一氧化碳。現在如果改成氫能和天然氣,那是沒有大問題的。
在和大眾生活密切相關的交通領域,氫能燃料電池驅動的車輛是否有競爭力?我們必須仔細分析綜合能效。內燃機車輛總能效平均只有20%,而電動車(乘用車)平均能效能夠達到80%,燃料電池驅動的車輛平均能效大概是36%,難以與電動車競爭。這也正是現在特斯拉和眾多電動車能夠輝煌的原因。
但是,如果是大馬力的卡車,特別是重卡車,或者物流車,這時電池的自重就成了重大問題,因為很大一部分電能要用來承擔車的自重,里程必然受到限制。氫燃料電池,具有一個顯著特點,就是單位質量的能量(注意不是單位體積)是最大的 —— 每公斤氫相當于40度電,是同樣質量汽油的3倍,是同樣質量鋰電池的100多倍,缺點是體積較大。那么在兼顧電池體積和質量(也就是總能量)的前提下,在體積相對較大的車輛上——卡車, 特別是重卡,物流車上,氫燃料電池就會顯示較強的競爭力。市場已經開始證明這一點,中國的路面上已經跑著將近1萬輛氫燃料電池物流車。

越是難減排的行業,氫能越有用
一些現有的行業是人類文明存在的基礎,但又是難以減排的,對此氫能有可能發揮獨特作用。比如鋼鐵工業,高爐目前主要是用焦炭作為主要燃料,鐵粉Fe2O3和一氧化碳CO發生氧化反應來生產生鐵,溫度高達2000度,要排放巨量的二氧化碳。但是如果是用氫做燃料,氫是還原劑,鐵粉Fe2O3 和氫H2發生還原反應,溫度只需到800-1200度,就可以生產出鐵(DRI技術)。另外,廢鋼可以在電弧爐中重新鍛造而得到循環使用,這其中的減碳效應也是非常可觀的。
在航運上,綠氫既可以通過轉化為綠氨直接使用,而且氫燃料電池還可以作為岸電系統給船舶充電。這能大大緩解目前航運使用重燃料油而帶來的嚴重污染。
飛行是當代文明的重要標志。由于氫能燃料電池體積較大的原因,它可以為短途飛行提供動力,但是長途飛行目前還沒有看到可靠的方案。但是生物航油也許可以另辟蹊徑解決這個問題。
航天就更清楚了,液氫一直是火箭升空的動力之一。如果2050年到火星旅行不再是探險科考,而是人類看宇宙的一個選項,氫能一定是少不了的。
在塑料,水泥領域,雖然還沒有成熟的技術立刻大規模減排,但使用氫作為燃料和原料的技術有很多已經在實驗室里。水泥的制造方法也許會發生革命性的變化,變成用二氧化碳作為原料的負碳行業。
氫能將是地緣政治新的穩定器
氫能不光是人類解決氣候變化危機的重要手段,也是許多國家的發展經濟的重要動力。沙特今天出口石油天然氣,明天就可以出口綠氫;北非今天通過穿越地中海的管道向歐洲輸送天然氣,明天則可以輸送綠氫;澳大利亞今天出口天然氣,明天也可以出口綠氫。氫能還將是全球地緣政治新平衡的重要媒介。
在歐盟激進的能源轉型方案中,氫能扮演重大角色,RePower EU計劃里設定的目標是:到2030年自產500萬噸,進口1000萬噸氫能。美國對氫能的政策支持力度更是前所未有。在2021年11月通過的兩黨基礎設施法案(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)給予氫能示范項目95億美元預算的基礎上,2022年8月出臺的通脹消減法案(Inflation Reduction Act)大幅提高了支出力度:按全生命周期計算,如果每公斤氫的CO2 排放低于0.45公斤,并且符合勞工條款,那么每公斤氫可以享受3美元的稅收補貼,這會極大促進綠氫的生產和應用。綠氫的規模生產,會刺激電解槽裝置容量提升成本降低,也會產生對光伏板的新需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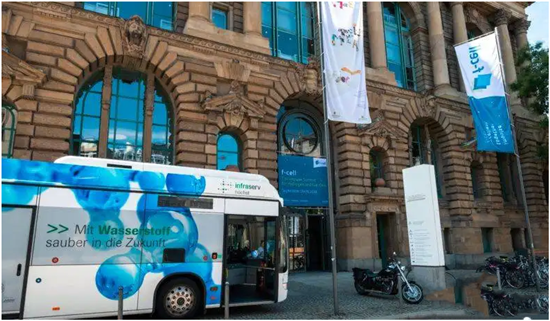
光伏板不用說,主要要靠中國生產,我認為GW級別的電解槽也會出自中國,氫能,將寫出全球合作的新篇章,成為全球化的新標志。當然這會是艱難的過程,充滿顛簸和挑戰。
有意思的是,在中國,地方政府和企業發展氫能的力度比中央政府更大。全國十四五能源規劃是到2025年綠氫產量10萬噸到20萬噸,2030年沒有具體的產量目標。但把各省市的規劃目標加總,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央政府的規劃。
放眼全球,氫能全產業鏈技術日益提高的成熟度,生產地域的開闊性,使用的便利性和廣泛性,減排的急迫性,多國政策前所未有的扶持力度,使得氫能的大規模應用不再是天方夜譚,而是可以觸摸的現實。也許,我們在2030年或者2040年回眸今天,一定會慶幸當初選擇了氫能,才得以化解讓地球洪水滔天的氣候危機。

近日,高德地圖聯合國家信息中心大數據發展部、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、同濟大學智能交通運輸系統(ITS)研究中心、未來交通與城市計算聯合實驗室等機構共同發布《2024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》(簡稱《報告》)。報告顯示,蘭州、合肥、濟南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數領先,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綠色出行意愿指數位列前三。 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數:蘭州、合肥、深圳領先 報告基于所監測的主要城市的公共交通數據,對城市公共交通的運行效率、可靠性以及用戶出行體驗進行了全面分析。數據顯示,蘭州市、合肥市、深圳市在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數方面表現突出,分別位列大中城市、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首位。蘭州市的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數最高,達到81.48%,顯示出其公共交通系統的高效性和可靠性。 從換乘系數來看,2024年期間,城市公共交通平均換乘系數整體同比去年呈持平或下降趨勢。東莞市、沈陽市、海口市的公交換乘系數分別在超大、特大、中大城市中最小,顯示出這些城市在公共交通系統設計上的便捷性。而在公交運行效率方面,臺州市城市核心區內的高峰期“社會車輛-公交車速度比”最小,小汽車速度是公交的1.95倍,顯示出其公共交通出行用戶體感良好。常州市的“全市全天線路運營速度...